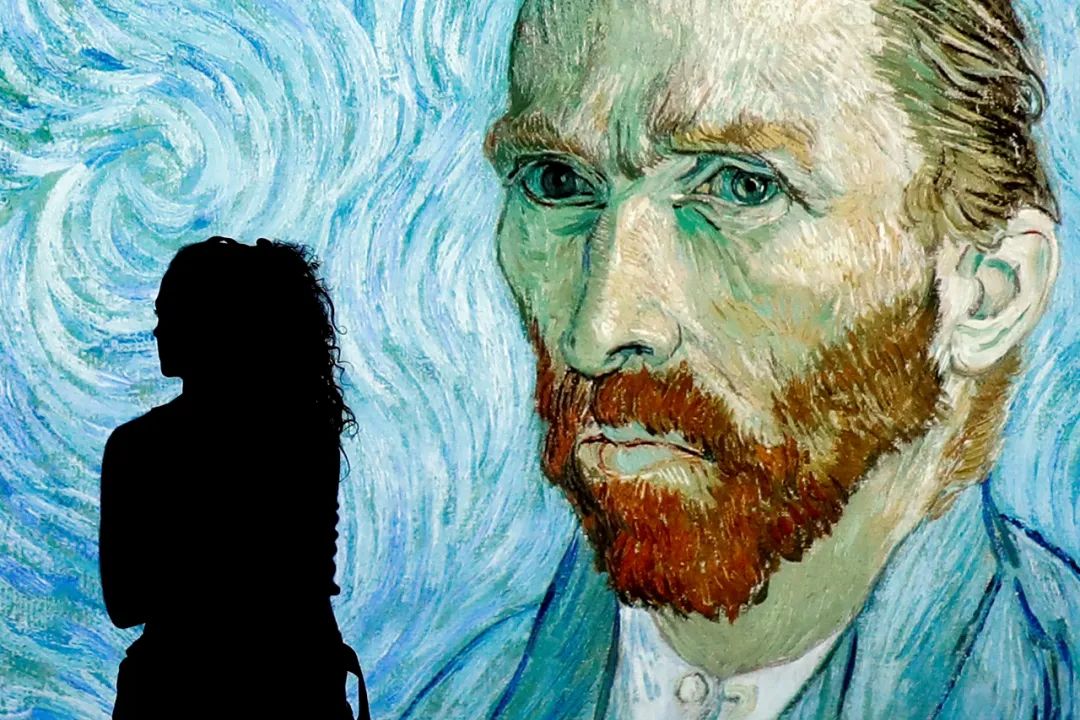作者:文嵊
小时候听一个大人说,县上的人在“厕缸脚”吃饭。“厕缸脚”用普通话说就是厕所边。大家不信,觉得不可思议,反复寻问,那大人说千真万确,否则天打雷劈。大伙信了他的话,对城里一贯的向往顿时消失,觉得县里人生活好奇怪、好可怜。
“厕缸”是那时老家的厕所,建在寨门附近,半截墙,没有封顶,其功能类似于现在城市里的公厕。大家需要上厕所往那里去——因为所有人家都没有厕所,女性方便就用眠床边布帘后一个带盖木桶,男性则统一去户外的“厕缸”。男性如厕擦屁股多数人是在路边捡几块小瓦片或是一些甘蔗渣,能用上旧纸张那是很奢侈的事。那个时候厕所是农作物重要的肥料来源,“厕缸”一般设在空旷而通风的地方,一般没有什么臭味。由于村里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厕所不远处也就成为人们聚集的地方。边上一颗树冠直径十几米的大榕树,大家在下面纳凉、聊天,时而有一些“讲古佬”过来讲古。村里的顽童经常在榕树下的厕所墙顶玩耍,有的还快速在墙顶走动,说是在展示《七侠五义》里展昭飞檐走壁的神功,惹得老人们心惊胆战。
尽管厕所边可以进行各种文体活动,但谁也不会把饭碗端去附近。村里仅有的几个卖粿条和虾饼的小店,也开在离厕所远远的地方。那时家乡人心目中,吃饭和上厕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厕所边吃饭,真是不伦不类的事。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位于县城的潮阳一中,我们宿舍楼用的是集体厕所,一直没看到县里的人在厕所边吃饭。后来有一天班主任老师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吃饭,才发现厕所和做饭的地方隔着一堵墙,吃饭的地方——那个时候不知道叫饭厅,真真切切就在厕所边上。那天我不知道其他几个乡下来的同学有什么看法,反正对我来说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因为很多很多东西是第一次见到。我告诉老师,几年来关于“厕边吃饭”的困惑终于揭开了。他忍俊不禁,说一般城里的家庭都是这样的,目前农村生活条件不好,以后经济发展了,慢慢也会这样的。之后,我人生中关于厕边吃饭的思考平息了很久。
大约四五年后,我再次遭遇并思考这个问题。那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和一个同学叔辉君结伴去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几乎开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穷游。我们背着行囊,从深大坐车去广州,从广州坐绿皮火车去昆明。历经辛苦到达昆明后,又从昆明坐长途大巴去景洪。一上大巴,我们两人衣着与其他乘客迥然不同。我们短衣短裤,而其他人基本是长衣长裤。我们彼此看对方都觉得奇怪。我们纳闷,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么多,可能他们纳闷我们为什么穿这么少。那个时候出门旅游还不流行做攻略,我们想着是大热天,根本就没准备御寒衣物。车子是夜间开出的,据说这条路一般不白天开,因为路边悬崖太陡峭,有的乘客会被吓到。由于旅途疲惫,我们上车后不久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两三点——我们其实是被冻醒的。本来吃得挺饱,由于一冷,热量流失厉害,很快就觉得饥寒交迫。
车在路上前行,不断改变方向,恍如一条在石块间蜿蜒游动的蛇,我们感觉身体忽左忽右的摆动,窗外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就在寒冷和饥饿要使我们无法忍受时,车子突然停下来,司机叫大家下车,说我们到了云贵高原海拔很高的地方,今晚没办法走了,就近休息,明天白天再走。我们两个哆嗦着下车,立即看到一个卖吃的地摊,我们也不晓得买的是什么,给了钱接过两大碗红通通的东西,囫囵地吃下去,整个人顿时温暖起来。
这时才看清楚司机的身材干瘦而独特,看上去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S。这位老兄告诉我们,旁边有睡觉的地方,价格很便宜——依稀记得一个铺位15元。我们跟着昏暗灯光摸到铺位,只见是一个可以睡几十个人的大通铺,我们拉上被子,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醒来,闻到很浓烈的臭味,才知道大通铺和两个厕所隔着一道不高的墙——味道告诉我们厕所应该是没怎么冲水的。仔细一看,发现我们半夜吃的是酸辣汤,吃东西的地方就在厕所的另一侧。司机说,山上平地不多,长途车中途休息点只能因地制宜,吃的地方、睡的地方和拉的地方才如此紧密团结在一起。
夜宿云贵高原那次是我人生头一回大碗吃辣味,也是我第一次吃睡都在厕所边。而这次遭遇,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我们两个愣头青从最低一层一下子朝第五层蹦跳,这样的经历使我们的蹦跳以更加斑斓的色彩存贮入记忆中。
后来,我看到关于大城市厕所里水箱的水在停水时可用于刷牙的说法。再后来,又看到我国一些地方修建五星级厕所、里面可以住人的报道……终于明白,我在人生不同时期听到、遇到和厕所有关的事,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昔日穷国前进的见证?如今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修建了自用厕所,昔日“厕缸”已不知所踪。尤其是广大农村掀起“厕所革命”后,各地厕所不断升级,一代比一代实用而美观,可谓厕外芳草萋萋,厕里洁净如雪。现在不少城市的厕所配之物,除了纸巾,还有洗手液、梳子、干手器以及放手机用的塑料小框。
我想,现在农村孩子听人说“厕所边吃饭”后,应该不会诧异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