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说起《茶馆》《骆驼祥子》《雷雨》你会想到什么?是老舍、曹禺、焦菊隐那些泰斗级的编剧、导演,还是秦怡、孙道临、于是之那个黑白影像里的璀璨群星,亦或是,它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一个高度虔诚的、统一的、经典的艺术时代。
今天的讲述者张定华,曾是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的秘书。作为北京人艺成长、发展的见证者,她以第一手材料记录了焦菊隐、曹禺,以及活跃在人艺舞台上许许多多著名艺术家的身影。
她说:“那一连串光彩夺目登峰造极的演出,那些才华横溢风格各异的演员,还有那生气盎然热闹非凡的人艺大院,无论我如何挣扎,也挥之不去。”
口述 | 张定华
数月之前,在悉尼家中,看了澳洲民族电视台播放的中国电影《变脸》。片子放完,已是子夜,从沙发上起来,移步到卧室床上,但辗转反侧,思绪泉涌,睡意全无。《变脸》的故事深刻感人,演员的表演出神入化,但触动我心灵的不仅是那故事,不仅是那表演,却是回忆。《变脸》的主角朱旭,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他的脸把我带回万里之外的故土,带回几十年前的往昔。北京人艺那一连串光彩夺目登峰造极的演出,那些才华横溢风格各异的演员,还有那生气盎然热闹非凡的人艺大院,在我面前一幕幕显现。无论我如何挣扎,也挥之不去。

我生在上海,因为妈妈张定华就职的《大公报》迁京,1953 年,我们全家搬到北京。大约一年多后,妈妈又调到北京人艺。北京人艺的全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北京的几个话剧团之一。抗战时期,妈妈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剧团,演了几年戏,有些名气。她是典型的戏迷。当朋友们建议她去演戏时,她竟毅然离开报社,去了人艺。
等她进去才知道,剧院里女演员很多,演戏的机会并不多。而剧院领导调她来,看中了她是记者,想让她来当笔杆子。她报到不久,就被任命为总导演办公室秘书。人艺的总导演即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隐。那时,我大概在上小学三年级。又过了一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星期天,我们家搬到了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56 号(现为20号)的北京人艺大院。

56 号人艺大院儿
那天奇冷,妈妈怕奶奶(因为外婆太拗口,所以我们从小管外婆叫奶奶)和我们四个孩子冻坏,就把我们带到她的办公室。等到家搬好,屋里安上烟筒、炉子,才让我们去新家。我这才知道,人艺的办公室是在一个非常考究的几进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不论正房厢房,都是雕梁画栋,拼花地板,而且全都装了护墙板和暖气,还有卫生设备,舒适之极。妈妈的办公室在北房的里间,大大的办公桌,高高的书架,很是气派。奶奶说解放前这原是大户人家的住宅,当时北京东西城的几大胡同里,这类考究的宅院不少。
我们搬进来后,才发现史家胡同里尽是很有气派的大宅院,特别是从胡同西口进来,过了史家胡同小学,路北一溜儿全是朱漆大门或黑漆大门的大院。小孩子好奇,总想伸头探脑地往大院里瞧瞧,也想知道到底是谁住在里边。不久,我们就探知,为北京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住在一个朱漆大门里,因为他的女儿跟我们同在王府大街小学。我们搬来之后,做过慈禧太后御前女官的裕荣龄搬进另一个大院。爸爸曾和一位朋友去拜访她。她写了一本《清宫琐记》,非常有趣。后来听说,毛主席敬重的章士钊也搬进史家胡同来了。有人考证,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培训学校”就设在史家胡同。前几批留美学生就在这里通过考试。其中包括后来清华的唯一的一位终身校长梅贻琦,文化名人胡适、赵元任和科学家竺可桢等。据说,清末名妓赛金花也曾住过史家胡同。小弟考入了史家胡同小学,据传说,史小的院子原是史可法的祠堂,但又有人说不是,只是一家姓史的大户的住宅。

整个大院住了几十家。还有一些人虽然不住在这个大院里,但天天要来这里上班、排戏,因之院里终日人来人往,好不热闹。56 号大门右边,就是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张长得又高又大,河北口音,一脸严肃,对大院里的孩子很有威慑力。传达室里有两部电话,不管是找谁的电话都打到那里。老张虽然不是演员,但嗓音一点不比演员们逊色。即使找住在大楼顶层的人,他站在楼下,两嗓子就把人喊下来了。大家要打电话也得去传达室,来信则都别在传达室窗前。因此,传达室就成了人来人往的中心。
在排演厅前有一溜儿黑板。剧院的告示都贴在黑板上,比如今天几点排什么戏,开什么会等等。要是公布了新戏的演员名单,黑板前就会围满了人,大家一面看,一面指指点点地议论。除了院长曹禺不常来人艺大院上班,其余的副院长、大导演、演员们,总是在院里穿梭来去。
最使我着迷的是人艺的女演员们。她们一般都很会打扮,一年四季穿着入时。特别是夏天,年轻的女演员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连衣裙,身材又好,真是美不胜收。记得有一年夏天,时兴浅色带点儿的连衣裙。那些年轻的女演员们人人一件,有的是淡黄带黑点儿,有的是粉红带白点儿,有的是浅绿带白点儿。她们在院里穿梭来去,就像时装表演似的,看得人眼花缭乱。那时,朱琳已不太年轻,大概三十多岁吧,但她总是化着淡妆,打扮得体,说出话来有板有眼,显得风姿绰约。
穿着最考究的是舒绣文。我家搬进56 号大院时,她刚从上影调到人艺不久。爸爸妈妈总说,中国电影界的四大名旦——白杨、张瑞芳、舒绣文和秦怡,数秦怡最漂亮,但最会演戏的则是舒绣文。那时,姐姐刚刚带我和大弟看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我对演坏女人的舒绣文印象很深。我当时看电影的水平仅是分出好人坏人而已。她演的阔太太抢了白杨演的纺织女工的丈夫,不是坏人吗?不过,在台下的舒绣文和《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不一样,她说的普通话软软的,带着南音,又总是笑容可掬。当时,人艺只有她、焦菊隐和曹禺是拿文艺一级的工资。院里的演员中,也数她名气最大、资格最老,但她并未显出飞扬跋扈。

电影界“四大名旦”:张瑞芳、秦怡、白杨、舒绣文
人艺的男演员们风度翩翩者大有人在。于是之那时大约三十岁出头,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目光锐利、深邃,总是显得若有所思。蓝天野不仅个子高,眼睛大,且声音特别洪亮深沉,他不爱说话,鲜有笑容,人像声音一样深沉。郑榕个子也高,但不那么英俊,他的声音深厚又略带沙哑。他们仨人在《茶馆》中演的王老板、秦仲义和常四爷,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堪称最佳搭配。

提起人艺的特色演员,我还想起一件事。1957 年,人艺的导演梅阡把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话剧,并亲自担任导演。那天,排演厅前的黑板报栏贴出了演员名单。当然,每个戏的演员名单不仅由个人申请,还要人艺党委和艺委会讨论通过才可定夺。大家都围上来看,连我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孩子也来凑热闹。
忽然,女演员金雅琴大哭起来。旁边的人急忙把她架到演员童弟和肖榴家中坐下。原来,演员名单上豁然写着,由金雅琴演跳大神的巫婆。她气得捶胸大哭。但她这么一哭,扯着嗓子一喊,倒让我觉得真有几分巫婆的“神气”。后来,不知谁把她劝好了。等戏公演之时,奶奶一个劲儿感叹:“金雅琴哼哼唧唧、神神叨叨的样子,太像旧社会的巫婆了。别说主角,就是这个巫婆,青艺、儿艺就拿不出来!”
2005 年底,81岁的金雅琴先后获得第18 届东京电影节和第14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影后称号。我看了她在凤凰电视台“鲁豫有约”中的访谈才知道,她原先申请演女主角虎妞。没想到演员名单一公布,是演跳大神儿的,非常失望。她还说,她当时在台上这么又哼又唱,观众乐得捶胸顿足。后来,书记说,坏了,这场戏是悲剧,虎妞要死,金雅琴一上台变闹剧了,就把这段戏取消了。可见,这段戏之精彩。
排演厅里的世界
自从搬进56 号,使我最为流连忘返的就是我家门前的排演厅。我每天下午放了学,拿上几块奶奶烤好的馒头片,就悄悄溜进排演厅。那里一年四季都在排戏。平时,常常台上排一个戏,台下用屏风隔开,又排一组戏。我们刚搬进56 号时,正在排郭沫若的《虎符》。
我那时小,对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自然不知道,但我却被排演厅里的一切迷住了。导演焦菊隐一遍遍地给他们说戏。演魏王的戴涯嗓音沙哑,又黑又胖,在我眼中太适合演这个坏蛋了。于是之演的信陵君风度翩翩,声音特别优美,又充满了忧郁。朱琳演魏王的妻子如姬,但她似乎又爱魏王的弟弟信陵君。她将画着虎的兵符偷出来,披着黑色披风,飘飘曳曳地来到郊外小桥边,把它偷偷交给了信陵君。信陵君深深作揖,依依告别,拿着虎符去前线调兵救赵。

我静静地坐着,傻傻地看着,被剧情弄得痴痴迷迷。演宫女的文燕被亲兵拉到后台去处死,焦先生说,她得跪着后退。她就和演亲兵的演员一遍遍地练习,她的膝盖在地板上磕得嘣嘣响。等这出戏在剧场彩排时,我们全家都去了。每出戏公演前,一般彩排两三次,院里的家属都会有票去看。
有一天,我正看得出神,妈妈来了。田冲伯伯见了妈妈,就笑着说:“定华,你这个女儿呀,看排戏真入神儿,看到紧张处,她嘴都张开了。”说着,他张开嘴,学我的傻样儿。妈妈大笑,我却很不好意思。后来,再看排戏,我总有意识地闭着嘴。
小说《林海雪原》出版不久,人艺就把它改编成话剧《智取威虎山》。排演厅里摆满了各种布景,有山石,有大树,有李勇奇家的小屋,有座山雕的太师椅。排这出戏时,不仅我,连大弟弟也整天泡在排演厅里。不管是童弟演的少剑波还是童超演的杨子荣,都让我俩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郑榕演的座山雕和他手下的八大金刚。郑榕个儿很高,但他弓着背,穿着一身黑衣,缩在太师椅里,讲话瓮声瓮气,甚是吓人。那八大金刚更是各有千秋。导演焦菊隐一遍一遍地让他们挨个表演。我记得黄宗洛身上嘀哩嘟噜地背着枪、短刀、烟枪、酒壶,显得别提多邋遢了。
黄宗洛的姐姐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演员黄宗英,他的哥哥黄宗江是剧作家,真可谓出身演艺世家。作为女人,黄宗英身材娇小,眉眼秀气,她在电影《家》中演得了肺病的梅表姐,惟妙惟肖。作为男人,黄宗洛个子也极小,五官不好看,两眼往下吊,大嘴往上翘。他的声音尖细,是所谓典型的公鸡嗓。他像黄宗英一样聪明,演戏特别会动脑子,因此,也特有光彩。他那阴阳怪气的公鸡嗓,那全身的嘀哩倒挂,如今我一闭眼还能想起他的样子。后来,他在《茶馆》里演提着画眉鸟的松二爷,真是绝了。

人艺排戏时,除导演外,剧中的老演员常常一遍遍地给年轻演员排戏,说戏。好多戏就是这样一段一段、一遍一遍地磨出来的。有一次,我悄悄溜进排演厅,看见于是之正给演祥子的李翔和演小福子的宋风仪排戏。宋风仪也叫宋雪茹,是朱旭的妻子。她长得清瘦秀气,声音凄楚,太适合演这苦命的小福子了。
那一场,虎妞病重,祥子抓回药来,邻居小福子进屋来用扇子扇火,帮祥子煨药。大概有一两分钟时间,台上只有小福子一人,而她并没有台词。她低着头上来,低着头扇火,反复几次,于是之都不满意。后来于是之拿过扇子给她表演一遍,又对她说:“小福子是配角、小角色,但在这一两分钟里,台上只有你一个人,你就是主角,你就成了大角色了,你要使出全身解数,尽情演好这场戏。”
宋风仪很感动,一个劲儿地点头,我当时心中一震,好像突然若有所悟。后来,我读到契诃夫的一段话,大意是,世上有大狗,也有小狗,但小狗也有叫的权利。作为普通人,我们都是小狗,是人生舞台上的小角色,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使出浑身解数,尽量叫得好听一点,活得精彩一点。
于是之虽然从解放前就演戏,但当时的名气并不大,只能算小演员。1951 年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他一下脱颖而出,后来他演信陵君,演《雷雨》里的大少爷,演《日出》里的李石清,在几年里就扎扎实实地奠定了他的大演员地位。不可否认,于是之是天才,但他的用功和努力是他成为中国话剧男演员第一人的重要原因。他在《茶馆》里演的王掌柜是实实在在的空前绝后。
多姿多彩的春节晚会
人艺每年都举行规模盛大的春节晚会,全院家属包括孩子们都在应邀之列,而节目之丰富,气氛之热烈,实在够我们这帮孩子长久翘望,兴奋良久。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人艺春节晚会是在灯市东口的人艺排演厅大楼举行的。那年,妈妈刚调到人艺,我家还未搬进56 号大院,因此,人艺的人我几乎全不认识。妈妈办公室的叔叔、阿姨很热情地来招呼我们,帮我们拿吃的、喝的。
那是一个各显神通的化装舞会。有人化装成白雪公主,有人化装成中国武士,还有一个人穿着一身紫色运动服,把一只紫色木桶套在身上,化装成甘蔗。妈妈穿着华丽的旗袍,化装成阔太太。她办公室的赵玉昌叔叔则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化装成她的儿子。
爸爸妈妈都说,董行佶化装的果戈理最像,是晚会的明星。董行佶身材瘦小,却相当英俊,眼睛大,鼻梁很高,嘴上戴了小胡子,与照片上的俄国作家果戈理惟妙惟肖。那时他相当年轻,但很会演戏,在《雷雨》中演二少爷,演得天真甜腻;在《日出》中演的胡四,则狡黠酸涩。记得奶奶对他赞不绝口:“董行佶才是个聪明人!他把胡四这小子演活了。你们没见过,旧社会在有钱人和交际花身边混闲饭的人,就是这副鬼样子。”
那次春节晚会之后,首都剧场盖好了,每年的人艺春节晚会就在首都剧场三楼的宴会大厅举行了。三楼平时不开,大楼梯上放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因此看演出的观众上不去。三楼大厅非常之大,中间有小舞台,两边各有小厅,出了大厅门还有一些小厅和房间。首都剧场是典型的法国式剧场设计,不但音响好,座位舒适,舞台设施先进,而且相当豪华气派。每层的大厅、休息室和大楼梯一色大理石地面。
自从春节晚会在首都剧场三楼大厅举办之后,规模也比从前大了,参加者除人艺的员工及家属,一些文化、体育界名人也常来参加,周总理来过几次。晚会开始时一般先表演小节目,然后就跳交谊舞。
记得有一个节目很有趣:黄宗洛变鸡蛋。黄宗洛瘦骨伶仃,喉结很大,两眼小而下吊,很像一只鸡。我想,他因此编了这个小品,逗大家笑笑。他在台上像母鸡般咯咯地叫着,好像马上就要下蛋的样子。和他搭档的女演员金昭则做出同情和爱莫能助的表情及手势在旁边着急。后来,咯咯了半天,他示意那鸡蛋从肚子里升到嗓子眼儿了,然后突然从嘴里变出来了一个大鸡蛋。全场老少哈哈大笑。
老舍先生自从1951 年把剧本《龙须沟》给了人艺,就偏爱人艺风格,就和人艺的演员、导演们成了朋友。每次春节晚会,他几乎都来。他是很放得开的人。一次,节目主持人说,请老舍先生讲笑话。我真没想到,他的声音这么洪亮,而讲的笑话又这么通俗。他说:有个傻媳妇,有一天,她在院里晾衣服。她婆婆说,你的动作真不雅观,屁股都撅到半边天上了。又有一天,人家问她,你知道天有多高吗?她就说,我知道,天有我的两个屁股高,婆婆说我一个屁股撅到半边天,我两个屁股不就是整个天了吗?他讲完,全场大笑。

曹禺作为院长,每个春节晚会是必到的。妈说,曹禺年轻时不但演过戏,还演得很好,但我不记得他在晚会上演过节目。和老舍相比,曹禺性格拘谨一些。郭沫若也来参加过人艺的春节晚会,但他既不演节目,也不跳舞,因此给我印象不深。实际上,人艺春节晚会的真正明星是周总理。
有一年的春节晚会,周总理来了。全场人都拥到大厅门口,然后又在大厅里围成一个圈,等着和总理握手。不管大人小孩,总理都笑容可掬地热情握手,还不时和一些人寒暄,谈笑。晚会气氛立即热烈起来,真是一人在场,满室生辉。
节目开始时,坐在前排的总理说:“李丽莲唱个陕北民歌好不好?”那时,欧阳山尊的爱人李丽莲在全国妇联工作。听说,解放前她去延安之前是演员,她在延安也常表演,因此总理知道她的歌唱得好。李丽莲瘦得袅袅婷婷,两只眼睛顾盼有神。被总理点名,她不好意思地站到了台上,唱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陕北民歌。她的声音圆润甜美,真像溪水般流畅。我这才知晓,陕北民歌如此之美。
那天,节目演完,总理就被人们簇拥到一头的小厅去休息。等大厅的椅子搬走,撒了滑石粉,音乐响起,总理又被女演员们拉出来跳舞。人艺的男女演员尽是舞场高手。我和姐姐最喜欢看他们跳舞,只要舞会开始,我俩就坐在舞场旁边不肯动了。尽管别的小厅和走廊里有各种可以得奖的游戏灯谜,我俩也不受诱惑。
总理被女演员们一个个邀请,我俩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妈,妈,快,快,你快去请总理跳舞呀,要不,总理走了怎么办?”总理被那么多人围着,妈妈不好意思挤上去。这时,正好跟总理跳舞的一个女演员被她的小孩抓住衣服叫走了,总理就迈着慢步,走下场来。我和姐姐眼尖,忙叫起来。妈微笑着迎上去说:“总理,我请您跳舞。”妈舞跳得极好,我和姐姐这时真为她得意啊!总理跳舞时步子很大,姿态潇洒,他的右手平平地放在妈妈的腰后,我们看得目不转睛。
那天晚上,总理走进大厅时,我和姐姐都站在妈妈身边,因此和总理握了手。后来过了好久,钻到别处去玩的大弟才来了。大弟比我小一岁,我俩从小就特别近。我埋怨说:“刚才,我们都和总理握过手了,你跑到哪儿去了?”我替他惋惜,因为总理走时不会再和大家握手了,要握也许要等到明年甚至后年。
大弟从小有蔫主意。他现出失望的神色,却没有讲话。一会儿,我看见总理向大厅外的厕所走去。等总理再进大厅时,大弟立即跑到门口,说:“总理,你和我握握手吧!”总理先是一愣,但立即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说:“好,我们握手!”看见此情此景,妈妈、姐姐和我自然而然地围了过去。总理和蔼地问我妈妈:“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吧?”妈说是。大弟的小脸兴奋得通红。我真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竟如此有勇有谋哩!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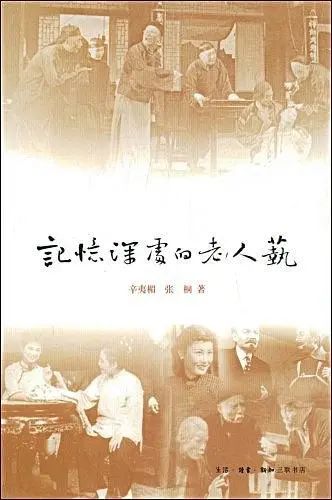
《记忆深处的老人艺》
作者: 张定华 / 辛夷楣 / 张桐
出版年: 2009-5




